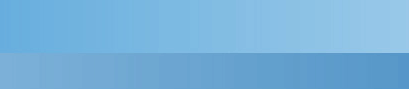迪高维尔转裁,原创作者:薛仁明
子曰:“士志于道,而耻恶衣恶食者,未足与议也!” 里仁篇
中国文明在复苏。首先要恢复士的自觉。
士的自觉,在于视野;视野辽阔,故不拘于窄隘之地。士的自觉,在于格局;格局宏大,故不执于六尺之躯,虽恶衣恶食,亦不足为耻。
晚周诸子,无一例外,全部都是士,他们是国士,更是天下士。他们志在天下,不斤斤于拘隘的地域国家。因不拘隘,故孔子离鲁而周游列国,冀望一展政治抱负,没人会訾议他为“鲁奸”;而孟子去邹而游于齐、梁,对齐、梁之君大谈王天下之道,也没人骂他“叛邹”,更没人怀疑他要“篡周”。同样的道理,屈原因贵族出身,对楚国情感甚深,其惓惓难舍,终至以身相殉,大家可以理解,也替他惋惜,却不觉得需要向他学习。
世人衣食多忧,天下士于此,亦切切于心,故不可耻于恶衣恶食。士若将富贵显扬、锦衣玉食视为当然,那么,对于所有民间疾苦,都将无法感同身受。对天下人之苦痛无感,则不足以言士。
中国读书人这士的自觉,历数千年,始终不辍。有此自觉,中国文明遂得以屡仆屡起;有此自觉,遂使中国文明向来是,有亡国家,而无亡天下。
这士的传统,后来断裂于五四运动。西方无此传统,故在全盘西化的浪潮中,士便渐渐隐去,取而代之的,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。
知识分子以知识学问为业,也关心国家社会的公共事务,乍看之下,与士相侔,但两者,其实不同。
不同之一,士以天下为己任,迥异于知识分子的动辄强调民族(国族)主义。士当然会有民族意识,却不落于民族(国族)主义。士的民族意识,只可以是种清朗的情感,不溺于情,不会有近代知识分子“献身”民族主义的种种举动。究极说,所有的“献身”,不管对象是什么,那都是种难以自知的巫魇。看来再如何伟大,但最终招来的,仍是不祥。
士的民族意识,毋宁是文明的。孔子严华夷之辩,无关种族,只是区别了文明与无明。孔子关心礼乐文明之重建,却不在意鲁国是否强大;同理,孔子称许管仲,也只因管仲维系华夏文明于不墬。对士而言,文明广被,泽及八荒,那才叫王天下。近代知识分子以传统文化为阻碍国家强大的绊脚石,必将自家文明去之而后快。这种视国家民族于文明之上的,只可以是知识分子,不可能是士。
士与知识分子,不同之二,是孔子所强调的,“士志于道”。中国文明,由“道”总绾,向来文、史、哲、艺、道一体。士为文明之载体,故必志于道。但知识分子不然;他们可以是专家学者,可以是通雅之人,然而,他们没有“道”的自觉。因为,在西方神圣与世俗二元论的传统中,“道”属于宗教,是神职教士之事,那无关乎知识分子。
中国文明没有这种二元分割,“士志于道”,“道”本修行之事,对士而言,志在天下与一己修身,两者本为一体;澄清天下与自家安顿,原是一而二,二而一。在中国文明里,志士的一生,就是一生的修行。
知识分子会因不公不义而浮躁难安,也会因社会乱象而愤懑怨怼,更会为了忧心时局而郁郁难解。但,士不然。“士志于道”,志士心里明白,士之首务,是自己心中,时时都要有个清平世界;如果自身都不得清安,如何期盼使天下人清安?一如孔子当年,外头的干戈,列国的倾轧,终究撼动不了他心头礼乐的风景明丽。那心头撼动不了的孔子,才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。两千多年来,因为孔子心头的风景明丽,因为孔子的笃定自在,遂有中国文明的恒亘绵常。而今往后的千万年呢?中国文明在复苏,我们也期待着士的新起!
作者系台湾作家,师从禅学大师林谷芳先生,私淑胡兰成,2009年出版《胡兰成·天地之始》引起轰动,2010年6月出版孔子系列合集《万象历然》。